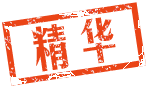第十五章:顽石与天命6 D7 |1 o$ d: X. r1 x+ s
4 e( |' @0 Y4 s. A
陆离走出太傅府时,天光正盛。秋日的阳光穿过高大的坊墙,在青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温暖而明亮。可这暖意,却一丝一毫也透不进他的骨髓。 他走得很慢,像一个大梦初醒的魂灵,在熟悉又陌生的神都街巷间游荡。周遭的喧闹——小贩的叫卖,车马的辘辘,孩童的嬉笑——都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壁障,遥远得如同另一个世界。 他的内心,是一座刚刚被抽空了神像的庙宇,只剩下空旷的回响和冰冷的基座。 那座神像,曾是他整个世界的支点。 他记得,少年时初入太傅府,因天资愚钝,连《论语》都背不周全,被同窗嘲笑。是太傅将他领到观星台下,指着满天星辰,告诉他:“书本上的道理是人写的,会骗人。但这天上的星轨,是宇宙的法则,至公无私。读懂了它,便读懂了天下最大的道理。” 他记得,有一年冬夜,他为了一道算学难题苦思冥想,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是太傅,亲手为他披上御寒的狐裘,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用那枯瘦却温暖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说:“痴儿,学问是用来济世的,不是用来折磨自己的。去睡吧,答案,有时在梦里。” 他记得太傅教他执笔,教他观星,教他弈棋,教他心算万物之理。那些温和的教诲,那些赞许的目光,那些视他如己出的慈爱……曾是他生命中最坚固的基石。 而现在,这座基石,连同建立于其上的一切,轰然崩塌。 原来,所有的教诲,都只是为了将他打造成最锋利的“磨刀石”。 所有的慈爱,都只是为了让他这块“悖论”更加完美。 他引以为傲的才华,他坚守不移的信念,在他最尊敬的恩师眼中,不过是一件用来淬炼“终极秩序”的、可笑的工具。 “为了一个绝对没有意外、没有纷争、没有痛苦的完美世界……” “人性,是我穷尽一生,想要修正的……唯一的错误。” 太傅的话语,如最恶毒的咒诅,在他脑海中反复回响。陆离的脚步猛然一顿,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扶着墙,剧烈地干呕起来。 他想象着那个“完美世界”——街上的人们面无表情,行动如钟表般精准;没有欢笑,因为欢笑是失序的;没有哭泣,因为悲伤是无用的;没有爱恨,因为情感是混乱的根源。整个神都,整个天下,都变成一座巨大、精密、却毫无生机的活人墓穴。 那不是安宁,那是墓园的寂静。 那不是秩序,那是对“人”之一字最彻底的抹杀! 一股混杂着恐惧与暴怒的烈焰,从他胸膛深处喷薄而出。恐惧于太傅那神明般冷酷的疯狂,愤怒于自己竟为这样的“神明”效力多年。那个在“桂花糕案”中死去的无辜孩子,那些在“归墟之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的百姓,他们不是必要的代价,他们是太傅用来祭祀他那扭曲理想的……祭品! 陆离抬起头,阳光刺得他眼睛生疼,泪水却无法流出。他看到街角那个卖糖人的小贩,正笑着将一个孙悟空模样的糖人递给一个雀跃的孩子。那笑容,那期盼,如此鲜活,如此真实。 这,才是他选择守护的东西。 不是冰冷的天命,不是完美的秩序。而是这尘世间,每一个会痛、会爱、会犯错的,活生生的人。 他不再迷茫。前路或许黑暗得望不见尽头,但他脚下的第一步,却从未如此刻这般清晰、坚定。他转身,朝着与来时截然不同的方向,大步走去。 那里,是三法司的所在。那里,有他的同伴在等待。 \6 j0 Z* X9 K. G0 e
$ Q; ^- M. m% z& M神都,清晨。东西两市的市鼓声刚刚敲响,坊门洞开,沉睡了一夜的巨兽便苏醒过来,吐纳着帝国最汹涌的人潮。这,便是陆离为他的故事选择的舞台。 此刻,他与狄仁杰正坐在西市入口处一家胡饼店的二楼,临窗而坐,俯瞰着下方川流不息的生命力。 “太傅的‘归墟’,视这片喧嚣为‘无序’,视这其中的情感为‘冗余’,”陆离轻声说,“他不懂,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我们的故事,就是要为这根基浇上火油。” 楼下,人群中几个毫不起眼的身影,在接到墨鸢发出的、一个几乎无法察别的暗号后,开始了行动。 西市最热闹的“丝绸巷”,一位盲眼的老乐师,怀抱一把斑驳的琵琶,开始讲述一个从未有人听过的故事。东市的“珍宝阁”前,一个落魄的书生,铺开一张画卷,高声说起画中人的传奇。 故事的名字很简单,叫《顽石传》。 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石痴”的石匠。技艺平平,家境贫寒。在他三十岁那年,一位自称能窥探“天机”的星官路过他的村庄,为村里每个人都写下了一份“天命判词”。 唯独给石痴的,只有寥寥八个字:“庸碌一生,无闻而终。” 村民们都信奉天命,劝他认命。但石痴盯着那张判词,沉默了三天三夜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将它付之一炬。 他说:“我的命,凭什么由一张纸来定?我的手,还没死!” 从那天起,他将全部家当换来一块巨大的青岩,立在院中。他不再接任何零活,只对着那块顽石,日夜不休地雕琢。他想雕刻一尊前所未有的神像——不是普度众生的慈悲佛,也不是执掌天条的威严神,而是一尊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抗争的“人”像。 “天命判词”上说,他四十岁时会因劳累过度而断掉右臂。到了那一天,他果然在挥锤时感到一阵脱力,巨锤险些砸向自己的手臂。可就在那一瞬,他想起了自己未完成的雕像,竟硬生生用左手格挡,任凭左臂骨裂,也护住了握刀的右手。 判词又说,他五十岁时会遭遇一场大火,家宅焚尽。到了那一天,邻家果然失火。众人皆逃,他却逆行冲入火海,拼着一身烧伤,将那尊已初具雏形的雕像拖了出来。 所有人都笑他痴,笑他傻。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执念,对抗着早已注定的结局,遍体鳞伤,何苦来哉? 石痴不言,只是日复一日,用他仅存的右手,继续雕琢。 判词上最后写着,在他六十岁生辰那天,天降雷霆,会把他和他的“悖逆之作”一同击为齑粉。 那天,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唯有石痴,将那尊耗尽他一生心血的雕像,推到了院子中央。他指着天空,用尽全身力气嘶吼: “来吧!看看是你这所谓的天命硬,还是我这双凡人的手硬!” 一道惊雷如天龙下凡,撕裂苍穹,直劈而下! -然而,雷声过后,预想中的灰飞烟灭并未出现。那道雷,没有击中石痴,也没有击碎雕像。它不偏不倚,正好劈在了雕像高举的、那只握着刻刀的手上!刹那间的高温,将闪电熔炼进了山岩,竟在青色的石像上,留下了一道道金蛇狂舞般的、绚烂夺目的天然纹路! 一场毁灭,竟成了一次鬼斧神工的“点睛”!那雕像,仿佛被注入了雷霆的灵魂,活了过来。 石匠看着自己的杰作,放声大笑,笑声中带着泪水。 他对着苍天喊道:“你看,我这一生,不是庸碌无为。我,留下了一件连你这老天都不得不为之喝彩的东西!” 从此,“天命”之说,在那片土地上,再也无人信服。人们只信,命,是自己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故事讲完了。 东西两市,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随即,如同滚油中被滴入一滴冷水,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怀疑、激动、压抑已久的愤懑与渴望,像病毒一样在人群中疯狂传播。《顽石传》的故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向整个神都的每一个角落蔓延。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而变成了一面镜子,一个象征,一个挑战“归墟之律”这至高权威的战书。
+ e9 z4 H5 M7 m" ~- N
5 F7 q) O. q; s
太傅府,静室。 巨大的星图沙盘上,代表神都的两市区域,原本平稳的数据流,正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剧烈的、无序的波动。无数代表着“质疑”、“抗争”、“悖逆”的红色光点,正以几何级数疯狂增殖,汇成一股刺目的风暴。 “太傅,”门生惊慌地禀报,“‘归墟’侦测到异常信息污染,是否立刻派遣金吾卫,抓捕所有说书人?” “不必。”太傅的声音冷得像冰。“抓人?那是凡夫俗子的手段。只会坐实我们心虚。” 他闭上眼,意识仿佛沉入了那庞大的主机枢之中。 “归墟,启动‘逆向溯源’。” “分析此次信息攻击的叙事逻辑、传播节点、行为模式。” “比对数据库中所有关键人物的智识特征、行事风格。” “目标锁定……陆离。” 沙盘之上,数据流光速运转。 “他们以为自己是猎人,”太傅睁开眼,眼中闪过一丝神明般的冷酷,“却不知,从踏入棋盘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一直是我的猎物。” 他的手指,在星图沙盘上轻轻一点。 “归墟,根据陆离的心理侧写与行为惯性,推演其当前最可能的藏身之所。” 沙盘上,神都的地图瞬间放大,无数光点闪烁后又熄灭。最终,只剩下西市边缘,一座名为“常乐坊”的区域,还在微微发光。光芒的中心,正是一家不起眼的、临街的胡饼店。 “找到了。” 太傅没有下令包围,没有调动一兵一卒。他只是对着虚空,下达了一个冰冷的指令。 “归墟,接管常乐坊周边所有巡街金吾卫、武侯铺的调度权限。调整巡逻路线,收缩包围网。无需突袭,无需抓捕。我只要……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 b3 _3 s( k* B" l
% z8 V, r' ]( m% p) C- q
* E, ^3 c m/ r5 q5 V- I第十六章:天算与人心
% N( E- R5 x- X& [: q& h- n7 s: ^# B% c% Y
胡饼店二楼的空气,仿佛在瞬间凝固,又被抽干。窗外依旧是那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神都,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窗内,却已是一座无形的、由纯粹逻辑构建而成的绝命囚笼。 “是‘归墟’。” 陆离的声音干涩而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艰难地挤出。他没有说“太傅”,而是直指那个真正的对手——那个由他亲手哺育长大的、冰冷的、无所不在的神。 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这不是人类指挥官的谋略,充满了试探、虚张声势与可能的疏漏。这是机器的“最优解”。每一队巡兵的位置,都像一颗落下的棋子,不多一分,不少一分,不多余,也无破绽。他们并非在“搜捕”,而是在执行一个已经计算出结果的“程序”。 墨鸢的身体紧绷如一张拉满的弓。她那双习惯于在黑暗中寻找生路的眼睛,第一次感到了茫然。她能看到街角的武侯,巷口的金吾卫,甚至能察觉到对面茶楼屋顶上,那个伪装成修补瓦片的工匠,其实是一名蓄势待发的弓手。他们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球体,将这栋小楼包裹在正中心。无懈可击。 “这是‘蜂巢式收缩包围’。”陆离闭上眼,脸上血色尽褪,“我设计的……专门用来对付最顶尖的刺客组织。它会模拟出十几条看似安全的逃生路线,但每一条路线的终点,都会触发更严密的连锁封锁。你跑得越快,网收得越紧。直到最后,将猎物所有的体力与希望,都耗尽在无用的奔逃之中。” 狄仁杰静立一旁,他是三人中唯一还保持着镇定的人。他深邃的目光穿透了眼前的危局,仿佛在审视一个更宏大的棋盘。 “陆离,”他沉声开口,“你既是它的创造者,就当知晓,世上可有完美的‘律’?” 陆离猛地一怔,抬起头,对上狄仁杰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睛。 “没有。”他下意识地回答。 “为何?”狄仁杰追问。 “因为……因为‘律’的建立,基于可被观测与计算的‘常量’。而这世上,最大的变数,是人心。”陆离喃喃道,眼中那熄灭的火焰,似乎被这句话重新点燃了一丝微弱的火星。 “然也。”狄仁杰颔首,目光扫过陆离,又落在墨鸢身上,“‘归墟’能算尽天时地利,能调度千军万马,但它算不到一个母亲为了救孩子能爆发出多大的力量,算不到一个朋友为了信义可以做出怎样的牺牲,也算不到……一个决心赴死的人,会选择何种方式,来撕开这片天罗地网。” 赴死?陆离像是被点醒了。对,‘归墟’的算法核心,是“趋利避害”。它的一切推演,都建立在“人是理性的”、“人是求生的”这一基础之上。 但如果……他们的选择,是非理性的呢?是“趋害避利”的呢? “我明白了。”陆离的呼吸急促起来,眼中那点火星,终于重新燃成了两簇跳动的火焰,“狄公,它能算出我们从哪里逃,却算不出我们敢于冲向哪里。” 他摊开一张随身携带的神都简图,手指重重地按在了一个点上。 “紫宸殿。” 狄仁杰与墨鸢同时倒吸一口凉气。紫宸殿,天子理政之所,帝国权力的心脏!擅闯紫宸殿,形同谋逆! “不,这恰恰是唯一的生路。”陆离的语速极快,“‘归墟’的包围网,是建立在‘抓捕钦犯’的逻辑上。它的权限,来自于太傅,但终究要遵循帝国法度。它可以在这里布下天罗地网,但它敢直接指挥金吾卫冲击紫宸殿吗?” 狄仁杰的眼睛亮了:“不敢。没有圣旨,任何武装力量胆敢靠近紫宸殿百步之内,格杀勿论。这是写进大唐律法,甚至高于‘归墟’权限的最高指令。” “没错!这就是‘律’与‘律’之间的冲突!”陆离的声音激动起来,“我们冲向紫宸殿,就是在用皇权的‘绝对逻辑’,去冲击太傅的‘抓捕逻辑’。这会在瞬间造成‘归墟’系统内部的决策混乱,哪怕只有短短一瞬间,也足够了!”
2 z) u* y) N4 n `) Q, B6 h
$ H5 \! h& x- p9 M胡饼店的后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三人如三道青烟,迅速融入了坊市内复杂错乱的小巷。他们的方向,与所有“归墟”计算出的逃生路线都背道而驰。他们没有走向城门,没有走向码头,而是如同一支逆流的箭,直指神都的心脏——皇城。 太傅府,静室。星图沙盘之上,代表陆离三人的光点,开始以一种决绝而诡异的轨迹移动。 “目标方向……皇城?”即便是太傅,脸上也第一次露出了一丝讶异。这不合逻辑。 “悖论……检测到逻辑悖论……”沙盘上,一行红色的字符闪烁起来。“目标行为将导致系统内部权限冲突。‘抓捕指令’与‘皇权守护最高指令’冲突。正在演算解决方案……” 太傅看着那行刺眼的红色字符,脸上终于浮现出一抹复杂的神情。有愤怒,有失望,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病态的……赞赏。 “好棋……好一个陆离。你终于学会了,用‘规则’本身,来对抗‘规则’。”他低声自语。 “但是,离儿,你还是太小看为师了。”太傅的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怜悯。“你以为,为师建立‘归墟’,会留下如此明显的‘漏洞’吗?” 他缓缓抬起手,从袖中取出了一枚小小的、由玄铁打造的令牌。令牌之上,只有一个古朴的篆字——“天”。 他将令牌,轻轻按在了沙盘的中央。 “归墟,”他用一种近乎咏叹的语调,下达了新的指令。“启动……‘天命’协议。” 嗡—— 整个星图沙盘,瞬间光芒大作! “‘天命’协议已启动。获得……最高序列权限。” “覆盖‘皇权守护指令’。” “所有禁军、金吾卫、城防军……临时调度权限,已接管。” “目标:紫宸殿。执行……‘清场’。” 太傅缓缓收回手,静静地看着那片星空。 “离儿,为师本不想走到这一步。” “你选择用‘人心’的混乱来对抗我,我便让你看看,在绝对的‘天命’之下,人心,是何其的渺小与无力。” “为师,亲自去为你上最后一课。” 他转身,步出静室。一辆朴实无华的黑色马车,早已静候在府门前。 “去紫宸殿。” 马车启动,悄无声息地汇入了神都的夜色之中。他没有带一兵一卒,因为他知道,整个神都,此刻都已是他的军队。
5 Y. e, B6 l) A1 `9 ^6 ~/ c! u# @
& {' h; W" A# r+ v+ q
) @4 _8 W- L. U/ q& _
第十七章:归墟之殇. V- N) \) F! W: h. L0 j3 {) b* G
: ~0 E6 Q L- N: I- r% v) m紫宸殿前,汉白玉广场。 皎洁的月光,如水银般倾泻而下,将这片象征着帝国至高权力的广场,染上了一层清冷而圣洁的霜华。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 狄仁杰手持金牌,站在百步之外。他的身后,是陆离和墨鸢。 他们的面前,是黑压压的一片禁军。这些帝国最精锐的战士,身披明光铠,手持长戟,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钢铁之墙。他们的眼神冷漠而坚定,身上散发出的杀气,仿佛能将月光都冻结。 然而,就在刚才,最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原本应该由禁军统领指挥的军队,在接到一道突如其来的指令后,竟然后退了三百步,重新布防,将整个紫宸殿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旷的、与世隔绝的舞台。而他们三人,就被晾在了这舞台的中央。 ‘归墟’,已经接管了禁军的指挥权。 陆离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随之破灭。太傅的权限,竟然已经大到了可以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地步。他们,还是输了。 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马蹄声,从广场的另一端传来。 一辆黑色的马车,缓缓驶入。车帘掀开,一个瘦削的身影,在月光下走了出来。玄色长袍,银发如雪。正是太傅。 他一步步地走来,步伐不快,却带着一种仿佛能踏碎山河的节奏。每一步,都像是踩在陆离的心跳上。他最终在陆离面前十步之遥的地方,停了下来。 师徒二人,在这帝国权力的中心,在这片空旷的舞台上,终于再次相对。 “离儿,你让我很失望。”太傅先开了口,声音里听不出喜怒,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你本是我最得意的作品,是我思想的延续,是‘归墟之律’最完美的执行者。可你,却选择与‘无序’和‘混乱’为伍。” “老师。”陆离迎着他的目光,声音虽然有些颤抖,却异常清晰,“学生只是选择与‘人’为伍。” “人?”太傅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你看看你身后这座城市。就在你们传播那个愚蠢故事的一个时辰里,‘归墟’记录到,神都城内,斗殴事件增加了三百七十二起,商铺毁约增加了八十九起,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争执,超过千起。这就是你想要的‘人’吗?充满了愤怒、贪婪、愚昧和自毁倾向的集合体?” 他的声音,通过某种未知的扩音装置,清晰地回荡在整个广场上。 “我赐予他们秩序,赐予他们安宁。我为他们规划好最平坦的道路,让他们免于饥饿,免于战乱,免于做出错误选择后所带来的无尽痛苦。我所做的,是最大的‘善’!而你,却用一个谎言,将他们重新推回了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混乱的深渊。你,才是在作恶!” “不!”一个清脆而坚定的声音,在此时响起。是墨鸢。 她往前一步,与陆离并肩而立,直面着太傅那神明般的威压。 “你说的那些,是‘养’,不是‘活’。”她的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你把人当成猪圈里的牲畜,喂饱了,就不许他们嚎叫。但人不是牲畜!人有喜怒哀乐,会爱,会恨,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念头,去做些明知会受伤的傻事。这才是活着!你那种没有痛苦,也没有快乐的日子,跟死了有什么分别?” “说得好。”狄仁杰也缓缓上前,站在了陆离的另一侧。 “太傅,”他沉声道,“自由的选择权,即便这选择会带来痛苦,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尊严。剥夺了这份尊严,纵使国泰民安,也不过是一座华美的……坟墓。” 太傅静静地听着,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看向陆离:“这就是你的答案?宁愿要混乱的自由,也不要安稳的秩序?” “是。”陆离抬起头,眼中再无迷惘,只剩下澄澈的决绝。 “老师,您错了。您想建立一个没有错误的世界,可您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陆离的声音,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 “您畏惧人心的变量,所以想用‘归墟’将它彻底消除。可您不懂,正是这不可计算的‘变量’,才是推动这世界前进的唯一动力。石匠的‘执念’是变量,他对抗天命的‘勇气’是变量;墨鸢姑娘的‘情义’是变量,狄公的‘法理’是变量;我站在这里,反抗我亲手创造的神,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变量!” “您要的,是一个终点。而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广场上,陷入了一片死寂。这是两种世界观的终极对撞。 太傅沉默了很久。他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眼神中那最后一丝属于“老师”的温情,彻底消散,取而代代之的,是神明般的冷漠与威严。 “执迷不悟。”他轻轻吐出四个字。“我给过你机会了,离儿。” “既然你如此信奉那不可预测的‘变量’,那么,为师就让你亲眼见证一下。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所有的挣扎,所有的变量,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他转过身,面向那黑压压的禁军方阵。他没有下令,只是轻轻地抬起了右手。 “等等!”陆离突然喊道。 太傅的动作停住了,他侧过头,用眼角的余光看着他,仿佛在等待他的“遗言”。 陆离深吸一口气,他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他还有最后一张牌。一张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会产生何种后果的牌。 他看着太傅,一字一顿地说道:“老师,您说‘归墟’算无遗策。那您……算到了吗?” 他猛地伸手,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高高举起。 那不是兵器,也不是令牌。 那是一卷陈旧的、泛黄的竹简。 正是记载着“归墟”核心算法的那卷——“归墟之律”的源头。 “您算到,我会毁了它吗?”
* k( O8 P, h# p a! M) K' P
" z" f. u% o' o# h- \ ~
( Q* K( g, @, A9 z; K太傅的瞳孔,第一次剧烈地收缩了一下。那卷竹简!那是‘归墟’的“创世基石”,是整个庞大系统最初的逻辑原点。更重要的是,陆离曾在这卷核心竹简上,留下了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隐藏极深的后门——一个足以在关键时刻,对整个系统造成致命干扰的“逻辑炸弹”。 “你要做什么?”太傅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一丝真正的惊怒。 “老师,您教过我,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陆离惨然一笑,双手开始用力。那看似坚韧的竹简,在他的内力灌注下,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咯吱”声。“我要证明给您看,任何号称完美的‘律’,都会有瑕疵。而创造它的‘人’,就是它最大的瑕疵!” “住手!”太傅厉声喝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颗“逻辑炸弹”一旦被触发,它会将一种名为“自我怀疑”的模拟人类情感,注入‘归墟’的底层判断逻辑中。一个开始“怀疑”自身正确性的神,将会是何等景象? “晚了!”陆离大吼一声,双手猛然发力! 然而,就在此时,一道快如闪电的黑影,从他身侧一闪而过。是墨鸢。 她没有去攻击太傅,也没有去阻挡禁军。她的目标,是陆离手中的竹简。 噗! 一声轻微的、利刃入肉的声音响起。 陆离只觉得手中一轻,那卷预备被捏碎的竹简,被一股柔和而坚定的力量带偏了方向。 而墨鸢,则直直地撞进了他的怀里。 陆离低下头,惊恐地看到,一截染血的刀尖,从墨鸢的后心处,透了出来。 而那把刀的刀柄,正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是他在最后发力时,为了防止有人抢夺竹简而下意识拔出的防身短刀。 在电光火石的那一刻,墨鸢做出了一个‘归墟’永远也计算不出的选择。 她选择了……用自己的身体,阻止陆离。 “为……为什么?” 陆离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抱着怀中迅速变冷、变软的身体,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温热的鲜血,迅速浸透了他的衣襟,烫得他灵魂都在战栗。 “不……值得……” 墨鸢的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她的脸上,却没有痛苦,反而带着一抹解脱般的、凄美的笑容。 “陆离……我不想……你变成……和他一样的人……” “为了……一个理念……毁掉一切……” “那样的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会写《顽石传》的陆离……” 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她的手,还紧紧地抓着那卷竹简,保护着它,也保护着陆离最后的底线。 “活下去……” 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了两个字。 然后,她的手,无力地垂下。 那双曾如鹰隼般锐利的眼眸,永远地失去了光彩。 天地间,所有的声音,仿佛都在这一刻消失了。 陆离抱着墨鸢的尸体,呆呆地跪在冰冷的汉白玉广场上。 他赢了吗?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他沉浸在与‘归墟’的逻辑战争中,却忘了,他身边的人,是有血有肉,会痛,会死的。 对面的太傅,久久地伫立着。 他看着跪在血泊中的陆离,看着那个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念”而死的女子,他那坚如磐石的世界观,第一次,出现了一丝微不可察的裂痕。 他算到了陆离可能会自毁,但他没有算到,也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个人,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去阻止同伴的“胜利”。 这是一种……他数据库中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归墟’的星图沙盘上,那代表着墨鸢的光点,在熄灭的最后一刻,标记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法被定义的词汇。 ——“守护”。 太傅缓缓地转过身,没有再看陆离一眼,也没有下令抓捕。他走回马车,声音里带着一丝前所未有的疲惫。“我们走。” 黑色的马车,悄无声息地,再次融入了夜色。 偌大的广场上,只剩下三个人。 一个抱着爱人冰冷尸体、彻底心碎的青年。 一个手持金牌、面容悲怆的老者。 以及,一具尚有余温,却再也无法睁开双眼的……江湖奇女子。 狄仁杰走到陆离身边,轻轻地将自己的外袍,披在了墨鸢的身上,盖住了那触目惊心的伤口。他没有说话,只是拍了拍陆离的肩膀。 陆离抬起头,他的眼中,没有了泪,也没有了恨。只剩下一片空洞的、比‘归墟’的星辰大海,还要死寂的……虚无。 8 m) X; ~; k- N: G
未完待续
{* \& X7 L, }2 K& W* X6 Z/ ?
5 N$ W2 T, _+ ~& E F0 K%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