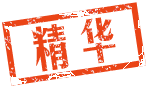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xiejin77 于 2025-7-30 16:12 编辑
8 l1 H4 X9 E, n) Q
' \7 c: n8 d; ~神都烟火志之半两食铺
* F; c5 \8 A) j# @+ e
K, ?: k$ L9 @! E* T& f: Z# c序章:亥时汤饼0 U1 K7 O4 t' L- |
武周天授年间,神都洛阳。 亥时初刻,暮鼓声早已沉入坊间的寂静。一百零九座坊,像一个个巨大的、沉默的石兽,匍匐在洛水北岸的棋盘格上。坊门落了锁,连缀的坊墙隔绝了月光,也隔绝了人间的声息。白日里车水马龙的天津桥,此刻只剩下桥下洛水无知无觉的呜咽,被寒风裹挟着,送入更深的夜。 这是属于金吾卫和更夫的时刻。铁甲的微光,木梆的脆响,是这片死寂中唯一被允许的律动。除此之外,神都已然入睡,睡得安稳,也睡得警惕。 然而,在皇城之南的从善坊,这片由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低阶文吏杂居的坊里东南角,却有一星灯火,倔强地刺破了浓得化不开的墨色。 那灯火并非来自高门大户的琉璃灯盏,而是从一间紧挨着坊墙的食铺里透出来的。铺子门楣上,悬着一块未经上漆的槐木招牌,借着屋内昏黄的光,隐约能辨认出三个阴刻的楷书字——“半两*铺”。字迹沉稳,不事张扬,如同这间铺子本身。门口那盏素面羊皮灯笼,在料峭的夜风里轻轻摇晃,光晕在湿冷的青石板上漾开,温暖得有些不真实。 冷的是高耸的坊墙,是空无一人的长街,是巡夜金吾卫盔甲上凝结的霜华。暖的是这一小方天地,是灯笼里跳跃的豆点火苗,是从门缝里溢出的一缕若有若无的骨汤香气。 冷与暖,仅一墙之隔,却像是两个世界。
2 x: `8 I1 L. V1 J. ~( o# O
9 W8 ^0 G* T; n R
食铺的门被推开一道缝,一个身影带着满身的寒气,闪了进来。排门合上的瞬间,也将外界的寒风与死寂彻底关在了门外。 铺内很小,一眼就能望尽。左手边是一个L型的榆木柜台,高及人腰,经年累月的擦拭,已磨出了一层温润的光泽。柜台后面便是半开放的灶间,一口大锅正咕嘟着,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灶后那人的面容。堂内只摆着四张松木方桌,配着圆形的蒲团坐墩,桌与桌之间隔得颇远,互不打扰。 柜台后的男人,便是这铺子的主人,韦掌柜。 他约莫四十岁年纪,一身再寻常不过的粗布短褐,却掩不住底下结实沉稳的骨架。他正背对着门口,专心致志地看着灶火。灶膛里的火光映在他的侧脸上,勾勒出平和的轮廓,鬓角处几缕过早的银丝,在火光中明明灭灭。他没回头,仿佛早就知道来人是谁,只是用低沉的嗓音问了一句: “老规矩?” 声音不响,却像投入静水的一颗石子,在满室的汤香中漾开。 来人是个老者,身形瘦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儒衫,背微微佝偻着。他解下被寒风吹得冰凉的头巾,露出满头花白的头发,点了点头,径自走向最里侧靠墙的那张桌子坐下。那是他的专属位置。 “嗯。”他应了一声,声音有些沙哑,像是久未言语的喉咙里磨出的锈。 一个穿着旧袄裙的少女,悄无声息地从柜台一角绕了出来。她约莫十五六岁,面容清秀,一双眼睛却像秋日里最清澈的溪水,能映出人心里最细微的波澜。她叫阿巳,是韦掌柜三年前雪夜里从坊门口捡回来的。她不会说话。 阿巳走到老者桌前,先用一块干净的棉布,将本就一尘不染的桌面又细细擦了一遍。然后,她回到柜台,取来一壶温好的米酒,两个粗陶酒杯,和一碟青瓷小盘装的醋芹。芹菜焯得碧绿,拌着几粒花椒,酸香开胃。她将酒壶、酒杯和菜碟轻轻放在老者面前,动作轻柔得没有一丝声响。 老者,铺子右舍的裴先生,曾是前唐太子詹事府的一位主簿。如今,不过是个靠代写书信、抄录经卷勉强度日的失意人。他拿起酒壶,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液浑浊,带着米香,是铺子里最便宜的。他端起杯,对着虚空晃了晃,像是在敬一位看不见的朋友,然后一饮而尽。辛辣的暖意顺着喉管滑下,他长长地吁了口气,那口气里,有酒气,也有散不尽的郁结。 阿巳没有立刻走开,她从怀里取出一块小小的木板和一截石炭笔,在木板上写了几个字,递到裴先生眼前。 “先生,夜寒,少饮。” 字迹娟秀,带着少女特有的认真。 裴先生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一丝暖意,他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答。阿巳这才收起木板,退回到柜台边,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拭那些码放整齐的粗陶碗,依旧悄无声息。 铺子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有灶膛里木柴偶尔爆出的“噼啪”声,锅里骨汤“咕嘟咕嘟”的沸腾声,以及裴先生一杯接一杯,酒杯与桌面碰撞的轻响。 韦掌柜自始至终没有回头,他从案板下抽出一团和好的面,放在撒了干粉的案板上,开始揉捏。他的手掌宽大,指节粗壮,布满了老茧。那双手,既有常年操持厨刀留下的印记,也依稀能分辨出更早些时候,紧握长柄兵器才能磨出的痕迹。他揉面的动作不疾不徐,力道均匀地渗透进面团的每一丝纹理。那不是在做食物,更像是在完成一种仪式,一种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他整个人都沉浸在那一团小小的面里,仿佛这方寸之间的揉、捏、拉、抻,便是他的整个世界。 铺子里的光线很暗,只靠着灶火和柜台上的一盏豆油灯照明。客人的脸,掌柜的脸,都在这昏黄的光影里变得模糊而柔和。每个人的心事,似乎也在这暖融融的氛围里,被熨帖得不再那么棱角分明。 ; K e( U/ V G2 i% _! s1 R
* u9 m$ D5 u, m; C/ \" e) Q! u又过了一炷香的功夫,排门再次被推开。 这次的动静大了许多,一个高大的身影裹着一身寒气和夜露闯了进来。他穿着金吾卫的皮甲,腰间的横刀在进门时与门框磕碰了一下,发出“铛”的一声闷响。来人是负责这片巡夜的武官阿狼,本名李景。 “掌柜的,一碗汤饼,多加些胡椒。”阿狼的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爽利,驱散了铺内些许的沉闷。 “知道了。”韦掌柜依旧没回头,只是手上的动作加快了几分。他将揉好的面团拉成细长的面条,再用刀切成一片片长短均匀的“汤饼”,随手一扬,面片便如下凡的仙女,飘飘扬扬地落入滚沸的锅中。 阿狼在靠门的桌子坐下,解下头盔放在一边,露出一张年轻而英朗的脸,只是眉宇间带着挥之不去的疲惫。他看到了角落里的裴先生,便朝那边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裴先生也抬起微醺的眼,回了一个礼。两人并无交谈,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阿巳端来一碗热茶,放在阿狼面前。阿狼对她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多谢阿巳姑娘。” 阿巳也弯了弯眼睛,算是回应。她知道,阿狼巡夜一宿,又冷又渴,一碗热汤饼下肚前,一杯热茶最能暖身。 很快,汤饼便好了。韦掌柜亲自用一个大木勺,连汤带面盛入一个粗陶大碗里。乳白色的骨汤,配上几片薄薄的白水羊肉,几根烫得刚好的青菜,最后撒上一撮碧绿的葱花和一大勺磨得极细的胡椒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他端着碗,从柜台后走了出来。这是他今晚第一次离开他的灶台。他将碗重重地放在阿狼面前,碗沿与桌面碰撞,发出的声音却沉稳有力。 “吃吧。” 阿狼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挑起一片汤饼吹了吹,便送入口中。面片薄而筋道,在浓郁的骨汤里浸润得恰到好处,羊肉酥烂,青菜爽口,再加上胡椒带来的辛辣暖意,一口下去,仿佛四肢百骸的寒气都被驱散了。他吃得又快又急,额头上很快便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韦掌柜没有回到柜台后,而是倚在柜台边,看着阿狼狼吞虎咽的样子,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久未归家的晚辈。 “今夜外面还太平?”他随口问道。 “太平,”阿狼嘴里塞满了食物,含糊地答道,“就是风大,刮得人脸疼。前几日抓到的那个偷儿,今天在西市挨了板子,估计能老实一阵子了。” “嗯。”韦掌柜应了一声,不再多问。 一碗汤饼很快见了底,连汤都被阿狼喝得一滴不剩。他满足地打了个饱嗝,从怀里摸出三文钱,放在桌上。 “掌柜的,走了。”他站起身,重新戴上头盔,推门而出。寒风瞬间倒灌进来,吹得豆油灯的火苗一阵摇曳。 铺子里又只剩下裴先生和沉默的掌柜与伙计。 裴先生壶里的酒已经喝完了,他没有再要。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桌上那盏快要燃尽的油灯,眼神迷离。良久,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韦掌柜听: “半生戎马,半生经纶,到头来,不过是求这半两残酒,偷得浮生半日闲……”他的声音很轻,充满了苦涩的自嘲。 韦掌柜正在擦拭阿狼用过的碗,听到这话,手上的动作顿了顿。他抬起头,目光穿过昏暗的光线,落在裴先生身上,缓缓说道: “先生,人生在世,谁不是在求那‘半两’?” 裴先生一怔,抬眼看他。 韦掌-柜将擦干的碗放回柜台,声音平静无波:“有人求半两功名,有人求半两富贵。到了我这铺子里,不过是饿了,求一碗半两钱的汤饼填肚;冷了,求一盅半两暖的浊酒驱寒。” 他顿了顿,拿起一块干净的抹布,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油亮的柜台,目光深邃,仿佛能看透着世间的百般滋味。 “我开这铺子,卖的是吃食,换的也不过是客官们口袋里那几文铜钱。” 他的声音沉了下去,像是说给自己听。 “或许,也想换一点别的东西。譬如,半两真情,半两故事,或只是……半两尘世里身不由己的欢愉。” 夜更深了。从善坊的这间小食铺里,灯火依旧。韦掌柜回到了他的灶台边,为那口永不熄火的锅添上了一块新柴。阿巳已经趴在柜台上,枕着自己的手臂,睡着了。 门外的风,似乎没有那么冷了。
6 _( | W& C9 }
: G6 M! h# f9 h6 A7 H8 q( ~
未完待续 ! k2 x, K4 ]; v+ k. l* ]
写了神都术数志两卷了,讲的都是些天翻地覆的大事,或者是庙堂之上的倾轧,或者是皇族巨宦之间的龃龉。既然开始写了,总不希望这么单调吧,干脆换个人间烟火的路线来讲些故事吧。 4 N6 V, ? {$ c* c2 w" x I- T' L
! n8 |; ^9 K) [9 G' _6 J) Y, D# r+ \2 M6 A* U
4 j& A% }8 S0 N7 m4 C% 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