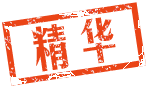|
背负者与探索者:作为“终极组织成员”的毛泽东 ——写在这一天,致那个独自承担历史重负的背影
6 ~. I0 c' A3 v$ `" }) W* Z& c3 z( G2 Q
4 t8 M: X+ n8 v% c+ c; c! I5 @
历史的迷雾终将散去,但历史的评价往往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在不同的河段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光影。当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下游回望,那个伫立在源头的身影,随着距离的拉长,反而愈发显得孤独而沉重。 , Q$ L- s' I9 j
长期以来,关于毛泽东的叙事往往陷入两种极端的庸俗化叙事陷阱:要么是光芒万丈、全知全能的完美神祇,不容许任何尘埃的沾染;要么是不可理喻、专断独行的独裁者,被视为一切苦难的根源。
' y& Q; C( @# H这两种叙事虽然在情绪上极具感染力,但在逻辑上也极其偷懒。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论,在解释我们这艘巨轮如何穿越20世纪最惊涛骇浪的峡谷、如何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惊险一跃时,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荒谬可笑。 . K' l1 ]) U' A. r! {% k- C
如果我们剥离掉那些神格化的油彩和妖魔化的污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冷峻眼光去审视,会发现一个被长期忽视、甚至被刻意回避的本质:
; _2 { p# }' d# k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伟大的领袖,更是我党这个超级组织中最彻底、最决绝,也是最孤独的“组织成员”。 * p8 \* V: [! D, m* L- W
一、 历史剧的残酷逻辑:要生存,还是要裤子?徐贵祥在《历史的天空》中,刻画了一个叫梁必达的草莽英雄。他要融入那个铁一般的革命队伍,必须经历脱胎换骨的剧痛。这种痛苦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流血牺牲,更是精神上的自我切割与重塑——是个人的散漫自由与组织的严酷纪律之间的撕裂,是小农意识的温情脉脉与工业化组织机器的冷酷理性之间的碰撞。
& h7 ~ [; Y# |' N4 F梁必达的成长史,本质上就是把一个“自然人”强行锻造为“组织人”的血泪史。 . n1 ^0 L0 m9 i- `; }- N
把这个逻辑放大到国家层面,就是毛泽东时代所面临的终极拷问。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如初入革命队伍的梁必达,面临着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而不仅仅是生活得好与坏的问题。作为梁的引路人杨庭辉,在开创凹凸山革命局面的时候和张普景有一番诚恳的对话:
* E' C2 b- K* }6 O4 Q* N) Z$ M$ B% y6 `
张普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让步,难道是被敌人吓破胆了吗?我们应该坚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不能妥协。” 杨庭辉说:“同志,斗争是要讲策略的,而眼下我们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发展我们的武装。只有当我们的武装力量相当壮大的时候,原则才有可能坚持得下去。如果我们一味蛮干,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那就是葬送我们的实力。”
6 r" q! A# ^% l/ E. h! Z
4 R" O8 C5 y1 U) A" S- Y
而这样做的结果是,杨庭辉背了妥协主义的骂名,还被张普景整了份材料;后来因为这个材料,被调离根据地去延安学习。
" C* @# D. r1 T& q
所以说这些权衡的决策者,往往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同时也是组织里最容易被诟病的人。但为组织负责,为人民负责而扛着这些前行的人,却往往会被从个人的角度去被脸谱化。 F/ @6 \0 c7 Q
当下的某些流行论调,习惯用“巨婴”的思维去裁剪历史,这是一种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傲慢。他们幻想如果当时不搞那些群众运动,不搞高积累的重工业建设,中国依然能自然而然地拥有今天的工业底子,同时人民还能在那个年代就吃饱穿暖,享受田园牧歌。这是一种极其幼稚且不负责任的假设。
, j7 y4 G; h: ~ P, r
作为这个国家的“当家人”,面临的是一个冷酷的死局: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要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生存,在资本主义列强的重重包围下站住脚,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积累。 # g0 f' o, u' w# q: _; v) Z4 i! u
钱从哪里来?技术从哪里来? 中国没有殖民地可供掠夺,没有马歇尔计划的输血,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这本质上是任何后发国家都无法逃避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中国表现为残酷的工农“剪刀差”——用农业哺育工业,用勒紧裤子省出来的资源来浇灌国家的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甚至是军事体系。 0 h. z) v6 _' x8 X" P/ L. x @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但同样残酷的战役。在他的主导下,我党选择了生存,选择了完整的重工业体系,选择了把国家安全的基石夯实,这就注定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要勒紧裤腰带,注定了消费品的极度匮乏。
- X0 F5 M+ b: V) e; B2 @
他不是不知道人民的疾苦,作为一个筚路蓝缕的革命者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农民的艰辛,但他更清楚“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铁律。在“让人民当下吃饱一点但国家随时可能被肢解”和“让人民当下受苦但国家拥有未来”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7 @ J# t2 Q9 A+ v
他以一种近乎残忍的理性,透支了自己在组织里的声望,甚至透支了人们对他的爱戴,前瞻性且高屋建瓴地强行将一个散漫的宗族社会下的农业文明拽入了工业文明的轨道。 作为组织一员的他为这个民族置换了一张进入现代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而这张入场券的价格,是那几代人的牺牲和他自己身后的骂名。 如果把这种基于国家生存的最高战略取舍,简化为个人的“好大喜功”、“不懂经济”或“性格缺陷”,这不仅是对历史复杂性的无知,更是对那些为了工业化而沉默牺牲的几亿农民和工人的亵渎。而另一方面,如果也仅仅是把这作为他个人的功勋,而忽略了这是我党的领导下的集体决策,就更是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我党作为先锋队,不是一个人的信众,而是基于使命感的组织。 % c v1 p3 Y# @- q; ~0 ]
: ~& Z. z3 i* q, O% r; \! L
二、 幸存者偏差与“替罪羊”的宿命9 R( I8 a9 o \2 q- b% e8 h4 ?
在《历史的天空》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关于那封“李文彬的遗书”以及党内复杂的清洗与甄别。李文彬之死,与其说是某个坏人的阴谋,不如说是那个特殊环境下,组织为了纯洁性而产生的过度免疫反应。 & {0 ?" H3 V$ _; U, e4 T- C$ C* U2 [
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上,像张普景这样原则性极强但也极度教条的干部,以及无数为了自保或邀功而层层加码的基层执行者,共同构成了运动扩大化的推手。然后又被万古碑之类的别有用心者作为自己可以利用的“势”,而借机在推波助澜中攫取权力。
. C( \6 w1 n% j8 n9 M# ~9 S( y
然而,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这种系统性的悲剧往往被简化了。只是由于毛泽东处于决策金字塔的顶端,他仿佛成了唯一的“恶人”,成了所有错误的唯一源头。
0 m0 o$ X& K: O4 h* d7 A3 |
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却也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必然。 政治运作中存在着显著的“幸存者偏差”。许多具体的执行者、推波助澜者,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并未处于最终负责人的位置,或者及时进行了政治转向,因此他们得以在事后洗刷责任,甚至以“受害者”或“纠正者”的面目出现,保留了完美的道德形象。他们在回忆录中,往往将自己描述为无奈的执行者或清醒的旁观者,而将所有的疯狂都归结于那个核心的意志。
' T! @% w A5 W
而毛泽东,作为“核心”,作为“主席”,他天然地成为了那个巨大的容器。 ' m/ Z+ E1 U0 ? L$ R1 c" M
改开后的中国为了轻装上阵,为了凝聚新的共识,需要一个解释过去几十年所有苦难的出口。体制的僵化、官僚队伍的素质局限、资源的客观匮乏、国际封锁的压力……这一切复杂的因素太难解释了,大众需要一个简单的符号来宣泄。 / V4 I7 j" d/ Z3 X
于是,毛泽东成为了承载这一切的唯一人选。 他替整个组织的官僚体系,替政治构建中的变化受过,替那个时代必然付出的代价受过,替无数在运动中推波助澜的“张普景、万古碑”们受过。他独自背负了本该由“历史必然性”和“集体无意识”共同承担的骂名。正如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他必须承担命运的诅咒,以便城邦得以净化。而这些只因为他认同他的组织,而他的组织的基础就是人民本身。 " f. v; R8 F% i* f0 z/ C, M2 D
8 t6 H+ T2 Y: L. z) @三、 求仁得仁:终极的“组织成员”
% R4 W V+ \( @/ d+ C2 C9 G$ U- M但从另一个维度看,这种评价对毛泽东又是“最公平”的。这或许正是他作为“终极组织成员”的宿命。 4 |: A/ A" ~. x& x D
不同于古代帝王维护家族血统的统治逻辑——帝王最恐惧的是权力的旁落,最在乎的是一家一姓的江山永固;毛泽东作为一个列宁式政党的领袖,他始终遵循的是“组织的逻辑”。 : e3 M; s! G/ l
他深知,既然拥有了定义路线的无上权力,就必须承担路线偏差带来的所有反噬。他一生信奉“内因论”,强调主观能动性,从不屑于将责任推给外部环境(如苏联逼迫、美国封锁)。 ) A1 Z, i; i6 t. L
当他晚年对身边人说出那句“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时候,他已经极其清醒地预见到了身后的风暴,预见到了自己可能会被描绘成什么样子。
5 N8 z+ l( \- G5 S& M0 U1 f E
但他依然选择了冲锋,像堂吉诃德一样,冲向那个名为“官僚主义”和“历史周期律”的风车。
3 Y2 O" b! j0 W7 e }' z
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最忠诚的“组织成员”。 在《历史的天空》中,我们看到组织是有生命的,它会老化,会僵化,会产生官僚主义的毒素,会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亲手缔造的这个强大机器,正在逐渐脱离群众,正在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正在变成它曾经反对的样子。 $ F# v/ |5 N% |" I ~, m! Y d% r
如果是为了个人权位,他完全可以在功成名就后垂拱而治,做一个被万世敬仰的“圣人”,享受“开国太祖”的尊荣。但他无法容忍组织的变质。 4 k$ R0 t" S, d8 |
为了对抗“历史周期律”,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他不惜亲手打碎自己建立的官僚科层机器,不惜发动一场注定失败的悲剧性冲锋,甚至不惜让自己从神坛跌落,承受“独裁者”的骂名,也要试图通过自下而上的冲击来通过这个“隘口”。 6 q3 C- U. W% @; b% W S' {
这绝不是帝王的权术,这是革命者的献祭。 帝王为了江山可以牺牲功臣,而革命者为了理想可以牺牲自己。他牺牲了妻子、兄弟、儿子,这些是肉体上的剥离;最后,他牺牲了自己的“完美”,牺牲了自己的身后名,这是精神上的凌迟。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把火,试图烧毁那些寄生在组织肌体上的腐肉,哪怕这把火最终也会吞噬他自己。 7 {, n8 k( p% }6 v
) ~0 X* i' `2 ]! P
结语
+ Q0 r; H2 C# M* F3 |4 W0 M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不是为了呼唤一尊新的神像,让他重新接受盲目的膜拜;而是为了读懂一个在历史夹缝中负重前行的巨人,读懂他在深夜里的叹息与坚守。
- u! G9 b4 |2 q( V
他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者,在没有路的地方硬是踩出了一条路。他确实犯过错,但那是一个试图在落后农业国强行开启工业化、在资本主义包围圈中强行探索社会主义新路的探索者的错误。他的错误,依然闪烁着理想主义的悲剧光辉,而非自私自利的卑琐暗影。 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把自己当作凌驾于众生之上的皇帝,而是把自己当作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用来对抗腐朽、对抗停滞、对抗历史惯性的最后一件武器。
. C* r' V- ?" r# h
他不仅是这个组织的缔造者,更是这个组织精神实质的守夜人。 哪怕这件武器最终折断了,他也无怨无悔。
$ e9 d7 }" D4 y2 a9 h: h" x
正如他那句震耳发聩的预言:
$ J, I4 N" b1 Z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 u; u. h$ D( q" T* g2 s& K
这就是一种极致的清醒,也是一种极致的公平。这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绝,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眼中,最真实的毛泽东。 " K1 m @# s( O) m9 R+ [' b% `
& C# P: G: [9 w4 G9 r2 J
7 {6 R7 ?$ c: B) p+ @
|